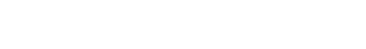思想史研究需要解析“微言”(即深奥的、没有明白表达的隐语),须还原文字,须合于事实,这都与中国传统学术“小学”有关。在研究中,我曾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陈独秀和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家章太炎同时也都是大学问家、思想家。他们在学术研究中所特别关注的学问之一竟然都是“小学”。前者在其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不顾病痛折磨,奋力编写的是《小学识字教本》,从事着音韵学研究;后者孜孜以求,终其一生的学术根基立于“小学”。这一现象所包含的学术意义、文化意义颇值得今人玩味,当另专文再论。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白的,这就是他们都认定“小学”乃实事求是之学,是中国文化学术之根。
我们还知道,从语言文字中也可以推断史实、证明史实。清代学者戴震的《字义疏正》和章太炎的《订文》,都提供了有益的指导,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汲取思想养料。
在中国近代,解析微言的范围要远远超出古代,不仅包括中文,亦涉及西文。同时,既要考虑西方文化的本源,又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学术。当年,李大钊赴日留学,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在日本(近代中西文化转换的中介)真正弄清楚西学的原委。因为当时有很多西学知识是从日本贩入中国的。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一方面倾心于西方法学,另一方面亦十分关注国内的制宪。李大钊特别重视从比较宪法学的角度,透过历史背景,对制宪理念、方法进行研究。他对比美国的制宪史,说明中国的制宪必然要经历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情况恐怕远比美国复杂。他解释说,“北美合众国长治久安之宪法,遂以改造于若辈之手,至今论政者传为佳话。愚之举此,以证新邦缔造之初,所制宪典,缺憾恒多未免,必经行之若干岁月,中间遭遇若干险阻,明达之士,烛识�紫龋�而谋以妥慎之方,总救其敝,方能奏长治久安之效也。愚非敢谓吾国今日与美国费府会议时情形相同,惟于经验一点,此等史迹,实足诏吾人以觉醒。彼自《联邦条规》施行以迄费府会议,中历十年。吾自《南京约法》以迄今兹,才弥五稔。以时日计之,适当其半,而以其间遭遇之险阻言之,其与吾人以严厉之教训者,千百倍之”。
在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以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同样抱有严谨科学的态度,尤为重视对概念、理论的解析。例如:他对民主和专政的认识就很有代表性和启发性。李大钊对我们所视为民主的概念做过专门的研究,但他一般不随意使用这一特定概念。因为他深感:“Democracy这个字最不容易翻译。由政治上解释他,可以说为一种制度。而由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去观察,他实在是近世纪的趋势,现世界的潮流,遍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几无一不是 Democracy的表现。这名词实足以代表时代精神。”
他认为,“民治主义,与Democ-racy的语源相符合”。但是,“现代的民主政治,已不含统治的意思,因为‘统治’是以一人或一部分人为治者,以其余人为被治者;一主治,一被治;一统治,一服从,这样的关系,不是现代平民主义所许的。故‘民治主义’的译语,今已觉得不十分惬当。余如‘平民主义’、‘唯民主义’及音译的‘德谟克拉西’,损失原义的地方较少。今为便于通俗了解起见,译为‘平民主义’”。
这里还应特别提及,1919年 1月,李大钊曾著文分析“平民独裁政治”(当时对阶级专政的一种译名)。他说,“俄、德起了社会革命,世人又造出一种新名辞来,叫做什么‘平民独裁政治’,就是说这种政治是平民一阶级的‘狄克铁特’(Dictator)。这话骤然听了,似乎可以成理,仔细想来却是非逻辑的。君主、贵族、资产阶级可以独裁,平民怎么能够独裁呢?平民不能尽化为君主、贵族、资本家,而君主、贵族、资本家都可以化为平民。平民政治的真精神,就是要泯除一切阶级,都使他们化为平民。你们若想做平民,那个不许你们来做?我们若想都做你们一样的贵族,是万万不能的。你们若想保存你们的阶级,那就是你们要独裁。所以我说只有君主、贵族、资本家的独裁政治,断乎没有‘平民独裁政治’。”李大钊的这段话表明,他完全不同意“平民独裁政治”的提法,因为它不合民主主义的逻辑,有悖于民主宪政的“真精神”。在他看来,平民政治就是“德谟克拉西”,即Democracy。它的最终目的在于消灭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的统治。“现代德谟克拉西的意义,不是对人的统治,乃是对事物的管理或执行。我们若欲实现德谟克拉西,不必研究怎样可以得着权力,应该研究管理事物的技术。”
(四)立足现时(事),反思历史
从现时问题出发,在历史过程中反思,着意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洞达未然。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也是它的基本目的所在。
这里,着实有必要重点分析一下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存在的两个重要的历史决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一般意义上,人们往往将其视为政治性文件。但我认为,它们是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思想史文献。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着眼,承史即诚实,在经历了磨难和灾难之后,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失误、错误,对自身的行动做出深刻的省思,并将反省付诸决议,这本身就是坚守实事求是的创举,也是非常典型的历史研究范例。它终将永久载入史册,启示后人。但遗憾的是,今天在中共党员中间,知道这两个决议的人似乎越来越少,甚至有人非议这两个决议。
在我看来,这两个决议的核心内容是立足现时,反思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第一个决议主要是反思中国革命。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在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就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时负责召集。经过历时11个月的准备,反复修改,数易其稿,终获认同。这一《决议》特别指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1931年1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因此,“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样的表述在政治文件中已经久违了,引者注),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做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决议》着重分析了“左”倾错误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的表现,以及“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应当说,整个分析是理性的、求是的、负责任的。
还应指出,这个《决议》的理论价值突出表现在对“左”倾错误的思想表现、思想方法的剖析,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而对犯错误的党内同志的恳切态度,又表现出政治上的理性和成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益。
第二个决议最引人注目是反思“文化大革命”。1981年6月27日,在时隔36年之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在历时一年多时间里,党内各方面人士畅所欲言、充分酝酿,先后经过中央书记处、4000党员干部、40多位党的负责同志、中央政治局、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的多次讨论,几经修改,七易其稿,最后终于形成了得到全党确认的“党的历史性决议”。如此重视总结党自身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决议》非常明确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我一直以为,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回归到20世纪80年代,一定要反思作为这一思想时代关键历史背景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承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理性特征之一就是从思想、理论到实践彻底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回归。实际上,逻辑和历史是一致的。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痛苦的磨难中开始了最深刻的反思,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这种反思的理性成果。我们看到,《决议》既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明确指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背离,及其产生的思想理论误区。《决议》勇于承担历史责任,毫不讳言党在实践当中的失误,而对于毛泽东的错误能够进行深刻的解析。《决议》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就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的境界。也正是在这样的理性认知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理论探索中才逐步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理念。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中重新审视两个决议,我觉得至少有三个主要特点需要在认知过程中给予充分的重视。首先,两个决议都是以“实事求是”为指导思想做出的。早1941年5月,毛泽东就针对中国革命的实践,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无独有偶,在1978年12月,为准备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又郑重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而开启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
其次,两个决议都涉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问题。它告诉人们,对领袖及其思想的评价至为关键,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必须对历史负责。因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但没有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当时只提“以毛泽东同志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专门论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其中最富有理论价值的部分是论证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同时指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再次,两个决议所反映的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为了保证其科学性,“决议”是通过民主的形式,经过党内同志畅所欲言,深入研究,在群言的基础上群策群力,逐步形成的。它有力地证明:只有集体智慧才是党的思想发展中产生思想力的源泉。
我们还知道,从语言文字中也可以推断史实、证明史实。清代学者戴震的《字义疏正》和章太炎的《订文》,都提供了有益的指导,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汲取思想养料。
在中国近代,解析微言的范围要远远超出古代,不仅包括中文,亦涉及西文。同时,既要考虑西方文化的本源,又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学术。当年,李大钊赴日留学,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在日本(近代中西文化转换的中介)真正弄清楚西学的原委。因为当时有很多西学知识是从日本贩入中国的。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一方面倾心于西方法学,另一方面亦十分关注国内的制宪。李大钊特别重视从比较宪法学的角度,透过历史背景,对制宪理念、方法进行研究。他对比美国的制宪史,说明中国的制宪必然要经历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情况恐怕远比美国复杂。他解释说,“北美合众国长治久安之宪法,遂以改造于若辈之手,至今论政者传为佳话。愚之举此,以证新邦缔造之初,所制宪典,缺憾恒多未免,必经行之若干岁月,中间遭遇若干险阻,明达之士,烛识�紫龋�而谋以妥慎之方,总救其敝,方能奏长治久安之效也。愚非敢谓吾国今日与美国费府会议时情形相同,惟于经验一点,此等史迹,实足诏吾人以觉醒。彼自《联邦条规》施行以迄费府会议,中历十年。吾自《南京约法》以迄今兹,才弥五稔。以时日计之,适当其半,而以其间遭遇之险阻言之,其与吾人以严厉之教训者,千百倍之”。
在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以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同样抱有严谨科学的态度,尤为重视对概念、理论的解析。例如:他对民主和专政的认识就很有代表性和启发性。李大钊对我们所视为民主的概念做过专门的研究,但他一般不随意使用这一特定概念。因为他深感:“Democracy这个字最不容易翻译。由政治上解释他,可以说为一种制度。而由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去观察,他实在是近世纪的趋势,现世界的潮流,遍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几无一不是 Democracy的表现。这名词实足以代表时代精神。”
他认为,“民治主义,与Democ-racy的语源相符合”。但是,“现代的民主政治,已不含统治的意思,因为‘统治’是以一人或一部分人为治者,以其余人为被治者;一主治,一被治;一统治,一服从,这样的关系,不是现代平民主义所许的。故‘民治主义’的译语,今已觉得不十分惬当。余如‘平民主义’、‘唯民主义’及音译的‘德谟克拉西’,损失原义的地方较少。今为便于通俗了解起见,译为‘平民主义’”。
这里还应特别提及,1919年 1月,李大钊曾著文分析“平民独裁政治”(当时对阶级专政的一种译名)。他说,“俄、德起了社会革命,世人又造出一种新名辞来,叫做什么‘平民独裁政治’,就是说这种政治是平民一阶级的‘狄克铁特’(Dictator)。这话骤然听了,似乎可以成理,仔细想来却是非逻辑的。君主、贵族、资产阶级可以独裁,平民怎么能够独裁呢?平民不能尽化为君主、贵族、资本家,而君主、贵族、资本家都可以化为平民。平民政治的真精神,就是要泯除一切阶级,都使他们化为平民。你们若想做平民,那个不许你们来做?我们若想都做你们一样的贵族,是万万不能的。你们若想保存你们的阶级,那就是你们要独裁。所以我说只有君主、贵族、资本家的独裁政治,断乎没有‘平民独裁政治’。”李大钊的这段话表明,他完全不同意“平民独裁政治”的提法,因为它不合民主主义的逻辑,有悖于民主宪政的“真精神”。在他看来,平民政治就是“德谟克拉西”,即Democracy。它的最终目的在于消灭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的统治。“现代德谟克拉西的意义,不是对人的统治,乃是对事物的管理或执行。我们若欲实现德谟克拉西,不必研究怎样可以得着权力,应该研究管理事物的技术。”
(四)立足现时(事),反思历史
从现时问题出发,在历史过程中反思,着意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洞达未然。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也是它的基本目的所在。
这里,着实有必要重点分析一下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存在的两个重要的历史决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一般意义上,人们往往将其视为政治性文件。但我认为,它们是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思想史文献。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着眼,承史即诚实,在经历了磨难和灾难之后,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失误、错误,对自身的行动做出深刻的省思,并将反省付诸决议,这本身就是坚守实事求是的创举,也是非常典型的历史研究范例。它终将永久载入史册,启示后人。但遗憾的是,今天在中共党员中间,知道这两个决议的人似乎越来越少,甚至有人非议这两个决议。
在我看来,这两个决议的核心内容是立足现时,反思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第一个决议主要是反思中国革命。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在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就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时负责召集。经过历时11个月的准备,反复修改,数易其稿,终获认同。这一《决议》特别指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1931年1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因此,“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样的表述在政治文件中已经久违了,引者注),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做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决议》着重分析了“左”倾错误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的表现,以及“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应当说,整个分析是理性的、求是的、负责任的。
还应指出,这个《决议》的理论价值突出表现在对“左”倾错误的思想表现、思想方法的剖析,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而对犯错误的党内同志的恳切态度,又表现出政治上的理性和成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益。
第二个决议最引人注目是反思“文化大革命”。1981年6月27日,在时隔36年之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在历时一年多时间里,党内各方面人士畅所欲言、充分酝酿,先后经过中央书记处、4000党员干部、40多位党的负责同志、中央政治局、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的多次讨论,几经修改,七易其稿,最后终于形成了得到全党确认的“党的历史性决议”。如此重视总结党自身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决议》非常明确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我一直以为,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回归到20世纪80年代,一定要反思作为这一思想时代关键历史背景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承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理性特征之一就是从思想、理论到实践彻底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回归。实际上,逻辑和历史是一致的。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痛苦的磨难中开始了最深刻的反思,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这种反思的理性成果。我们看到,《决议》既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明确指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背离,及其产生的思想理论误区。《决议》勇于承担历史责任,毫不讳言党在实践当中的失误,而对于毛泽东的错误能够进行深刻的解析。《决议》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就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的境界。也正是在这样的理性认知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理论探索中才逐步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理念。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中重新审视两个决议,我觉得至少有三个主要特点需要在认知过程中给予充分的重视。首先,两个决议都是以“实事求是”为指导思想做出的。早1941年5月,毛泽东就针对中国革命的实践,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无独有偶,在1978年12月,为准备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又郑重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而开启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
其次,两个决议都涉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问题。它告诉人们,对领袖及其思想的评价至为关键,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必须对历史负责。因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但没有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当时只提“以毛泽东同志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专门论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其中最富有理论价值的部分是论证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同时指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再次,两个决议所反映的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为了保证其科学性,“决议”是通过民主的形式,经过党内同志畅所欲言,深入研究,在群言的基础上群策群力,逐步形成的。它有力地证明:只有集体智慧才是党的思想发展中产生思想力的源泉。